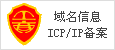《女驸马》是在《天仙配》之后又一个获得广泛影响的黄梅戏代表剧目。

《女驸马》是在黄梅戏传统剧目《双救主》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双救主》不属于黄梅戏“三十六大本”之列,新中国成立以后,安徽省潜山县老艺人左四和献出这个剧目的抄本,1958年,由安庆专署黄梅戏剧团将它改编整理(王湛、杨琦执笔),更名为《女驸马》,剔除了原作中的封建糟粕,并丰富了剧作的内容,排练后参加了当年安徽省第二届戏剧会演。1959年,安徽省黄梅戏团在安庆改本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加工提高,形成了新的演出本,由陆洪非执笔,遂使之成为继《天仙配》后又一个影响广泛的黄梅戏代表剧目。
《女驸马》描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冯素珍与李兆廷因父亲同朝为官,从小就同窗共砚,有了感情,两家也订下了婚约。然而数年以后李兆廷父亲遭受陷害,家道衰落,冯素珍的父亲冯顺卿和她的继母在李兆廷前来借贷时提出退婚,将冯素珍许配京中的刘大人之子。冯素珍暗中赠银李兆廷,被家人发觉,冯顺卿遂将李兆廷诬为盗贼。冯素珍为救李兆廷,女扮男装,冒名进京应试,得中头名状元。岂料皇帝在宗师刘大人的作伐下招她为驸马。此时冯素珍也找到了失散多年已为八府巡按的哥哥冯益民,但冯益民也无良计救她。在洞房之中,冯素珍向公主道出真情,又晓以利害关系,使公主不得不帮助她向皇帝求情,终于化险为夷,冯素珍被皇帝招为义女,与李兆廷团圆,公主也与冯益民成婚。
与《天仙配》的悲剧基调不同,《女驸马》以喜剧为其风格特色。它描写的是一个弱女子的胜利和封建家长、官僚乃至帝王失败的故事,剧本前半部虽有悲愁场面,但就整个剧本而言,它洋溢着斗争的欢笑和胜利的愉快,给观众带来的审美愉悦是——笑。
喜剧的创造,有赖于对人物性格、行动的“不和谐”因素的挖掘。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中说道:“本质与现象之间及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每一种差异都是滑稽可笑的,由于这种矛盾,现象全被取消,而目的在实现时成为笑柄。”别林斯基也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一观点,认为“喜剧的要素是生活现象与生活本质、生活目的之间的矛盾”。生活中的“不和谐”现象很多,被作家写入文学作品中,又必然带上一定的道德评判,由此又形成了歌颂性喜剧与讽刺性喜剧。《女驸马》的喜剧艺术风格,正是建立在对人物性格、行动和生活情境的“不和谐”因素创造的基础上,同时歌颂与讽刺并举,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冯素珍是剧中被集中歌颂的女性,作者为她设置了两重“不和谐”情境,一是女扮男装,二是考中状元。男性身份要求她假扮庄重,而状元身份更要求她遵从礼仪、文质彬彬,同时,还要时时保持这种男性状元的身份,不能泄露女儿之身的秘密。然而,作者又赋予她天真活泼的性格层面,于是在“状元府”一场中,性格与身份的不和谐便产生了:唱过“为救李郎离家园”一段后,春红喊她“小姐”,她提醒对方“嗯——”,春红急忙改叫“状元公”,她答应后,却又叫起“春红”来,又为春红所提醒改叫“李龙”。这样的不和谐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接着,第二重不和谐的情境出现,她本是女状元,却被当做男状元招为驸马,“不识奴家真面目,招我红妆为驸马”,“洞房”一场的开始,作者就用一段幕后伴唱突出了这一不和谐情境:
女:龙凤花烛耀眼明,洞房之中喜盈盈。
男:他那里紧锁双眉心不定,
女:她那里满怀喜悦做新人。
男:他那里心惊胆又战,
女:她那里一心一意结同心。
男:他那里假把诗书读,
女:她那里脉脉含情看郎君。
男:一个喜来一个忧,
齐:红妆一对怎能配婚?
不和谐之处正是“红妆一对怎能配婚”。正是在这一情境之中,冯素珍的聪明才能得以充分展现,先劝服了公主,又与公主在金殿上戏弄了刘大人和皇帝,巧妙地保护了自己,赢得了胜利。
与对冯素珍的歌颂相反,作品对刘大人和皇帝进行了嘲弄和讽刺。刘文举既聪明又糊涂,聪明在于熟悉官场奥秘,处处迎合圣意,尽献媚讨好之能事,以求“升官又加封”;糊涂在于为皇帝招了一个女驸马。这两者构成了他性格的矛盾,表现为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不和谐。“金殿”一场戏中,他夸赞着冯素珍的才貌:“老臣我天下举子见过千千万,从未见过像驸马这样博学多才,真是皇家的栋梁,我主的洪福,公主的如意郎君。”明为夸驸马,实则向皇帝、公主邀功,然而他的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相距太远,却丝毫不知道自己为皇帝招的是个女驸马,聪明建在糊涂的沙滩上,丑力求自炫为美,喜剧性就愈加强烈。当冯素珍身份明确后,冯益民前来请罪时,刘文举又想出个“好主意”,建议招冯益民为驸马,他夸赞冯益民:“眉清目秀美容貌,满腹经纶文才高,天下举子我见多少,只有他才算得当今英豪。”刚才夸过冯素珍的话这时又重复了一遍,前后态度、言语的不和谐表现了他为升官加封而邀宠献媚的丑恶本质,愈加可笑。在这一场中,作者还巧设戏弄的情境,让刘文举和皇帝自我讽刺。冯素珍将自己的经历编为前朝“故事”讲给他们听,皇帝说:“那个皇帝真是太糊涂了。”刘文举也随即附和:“那个媒人也是有眼无珠呀!”“要是出在我朝,定要定他一个失察之罪!”然而他们全然不知,自己就是那糊涂的皇帝、有眼无珠的媒人,主观认识的错误使他们出尽洋相,成为笑柄。
鲁迅说,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莫里哀说:“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最尖锐,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打击。责备两句,人容易受下去;可人受不了揶揄。人宁可作恶人,也不要作滑稽人。”《女驸马》对刘文举和皇帝的描写运用的就是这样的讽刺笔法。特别是刘文举的形象,是一个否定的喜剧形象,作品深刻揭示了他身上的“无价值”和“恶习”,让他变得滑稽可笑。对刘文举、皇帝否定的笑与对冯素珍肯定的笑构成了《女驸马》笑的二重奏,使它以喜剧艺术的精品列之于黄梅戏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优秀戏曲作品之中,成为深受观众欢迎、影响广泛的代表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