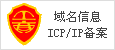二王行书并不是行书“书体”的源头,但绝对是后世行书“风格”的主要源头。

被李世民认为“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王羲之传论》)的王羲之,以创“新体”而成为领袖群伦的书史“第一人”。他所创的“新体”之一,正是行书。
在王羲之前,行书已然是一种通行的书体,如汉朝简牍中的早期行书,后世已不能见但载于史乘的刘德升、钟繇、胡昭以及王羲之师承的卫王,为王羲之以前的行书勾勒了一条显明的线索,特别是由钟繇而下以至卫王的行书风貌,在王羲之生活的早期,则是文人士大夫效法的书写风范,是当时的一种“流行体”。我们从后世出土的《李柏文书》推测,这种“流行体”在笔画连带、体势增长的同时还保留了隶书的一些笔画牲特征,因而畅达与凝重、风神外耀与朴质内敛兼而有之。王羲之的“新体”源于这种“流行体”(如传为王羲之的《姨母帖》即与《李柏文书》有不少相类处),但“力兼众美,会成一家”(清宋曹《论草书》),他在不断地实践中,逐渐改写了行书的书写“法则”,减去书写中的隶意,而出以迅捷爽直,体态上则易扁为纵,更加强调笔势的连贯和挺劲,从而将行书风格转换为一种“清劲妍美,遒润畅达”的新面貌,而且“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变法而成“新体”,使行书书体趋向完善,也使行书创作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身为王羲之的传人,王献之很好地继承了其父的艺术风范,特别是在行书上,“子敬才高识远,于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张怀《书议》)。从世传王献之的若干行书帖(如《廿十九日帖》、《地黄汤帖》等)看,献之行书在精神层面上确实与其父一脉相承,萧疏洒脱、妍美流畅是审美主调。但是,献之行书体势更为宽博,造型更为端严,笔法上则由内捩而为外拓,意态上也更见放纵自如。“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之独绝也”(张怀《书断》)的缘故,王献之在传承父亲精神内容的同时融入了张芝的形式语言,所以,他的行书大都偏向于草,偏向于开扩纵横,后代许多草书家往往于此取法。谓王献之“更开一门”,“独开门户”,立论正在于此。而且,王献之的“外拓”笔法也开启了行书体的另一法门,颜真卿于此即受益非浅。
初唐之世,由于太宗李世民酷爱羲之书法,并尊羲之为“书圣”,而使王羲之行书大放光彩(虽然李世民尊大王,抑小王,但小王与大王的血肉关系,似乎无法割断),初唐的书风也就与王羲之一脉相承。初唐习王之风蔚为壮观,一纸《兰亭》,既有著名的冯承素摹本,又有褚摹兰亭、传欧阳询临摹本《定武兰亭》、虞世南临本等等,《兰亭序》俨然而成“天下第一行书”。李世民行书自本于逸少,却因其帝王风采而更添雍容温雅之态。“初唐四家”虽主要在楷书上承继二王风韵,但所书行书也无不得之于二王:虞世南得二王之萧散,褚遂良得二王之清劲,欧阳询得二王之秀健。而陆柬之《文赋》更是一派《兰亭》风骨,遒劲、温润,“唐人法书,结体遒劲,有晋人风骨者帷见此卷”(元揭溪斯语)。总而言之,在李世民的倡导下,在一朝文人的群效之中,二王行书体系在初唐终成大势,成为书法史上的一大景观。自此而后,直至清代倡碑,几代行书书家,莫不模范二王,或在二王的胎体上刻意创新,另开一系。二王行草的传承,蔚成书法史上的“帖学”大宗。
米芾,无疑是二王行书体系中的重镇。米芾的皈依二王,是由唐颜、柳、李邕溯源而上的最后选择。米芾以“集古字”为荣,在二王体系中纵意取法,“取诸长处,总而成之”(米芾自述)。米芾之“成”,积聚着一生“集古”的深厚功力,更凝结着他天性近“颠”的叛逆精神,羲献的闲雅、洒脱,他心领神会,并以“刷”法、以“八面出锋”,而成“风樯陈马,沉着痛快”(苏轼《东坡集》)之夭矫自如的崭新面貌,羲献的“俗姿”,则力避之,“吾书无一笔王右军俗气”(董其昌《〈东见帖〉跋》引米芾自述)。笔法上,米芾将侧锋疾“刷”与中锋劲行糅合一在二王基础上有着创造性的发展,结字上的欹侧源于李邕但更为恣意、飞动,为行书重塑了勃勃的生机,从某种意义上说,二王行书的精神魅力,在米芾手上才得到了淋漓的体现,甚至可以说二王在米芾身上实现了“凤凰涅磐”,因为米芾,二王行书体系更加熠熠生姿。而米芾也就在二王大体系中开创了自己的行书小体系。米芾之后,大量的书家追随其侧,如米友仁、吴踞、王庭筠等等。当代书坛,学米更成时风,其中内奥,堪让人回味再三。
与米芾同时的薛绍彭,被人称为“独得二王笔意”(宋危素《薛临〈兰亭叙〉跋》),今人尹旭也称其与二王“形神俱肖,足以乱真”(《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他的这种真实地传承晋人雅韵,为二王行书体系的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铺垫作用。
如果对宋人行书尚意与二王行书的关系作一个总体性的评述,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二王行书为宋人尚意提供了先天的“动力”,让宋人之“意”能够具有历史的厚重和现实的丰富,而宋人尚意则使二王行书重放异彩,使二王行书体系形成更为壮观的书史系统。宋人尚意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更是一种历史的发展。
但在元人看来,宋人书法却是“去古已远”,于是,就有了以赵松雪为代表的元人书家对二王书法的“复兴”。赵松雪“惟于行书极得二王笔意”(陶宗仪《辍耕录》),力振南宋以来二王行书体系的衰竭气象。赵的行书在全力继承二王笔法、风韵的同时,更为儒雅飘逸,一派文人气息,使二王体系增添了新的意蕴,另外,赵松雪将草、行、楷笔法全力贯通,所作或为行楷,或为行草,或为纯行书,皆注以二王的晋人品格,大大丰富了行书的表现力。作为二王体系中的一代宗师,赵松雪的“复古”其实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发展。其他如鲜于枢行书于二王之雄劲处精研而成,康里子山行书在二王清隽中力学而出,皆成一代大家之格。而赵体行书之笼罩整个元代书坛,则已然是二王行书体系的一种“变相”普及。“复古”为二王行书在一个时代获得生机,而“普及”则不可避免地使二王行书体系走向媚俗。
明代前期,大多行书书家仍为赵书所范围,他们借赵而窥二王,然离二王已远。至中叶后,才稍有改观,祝允明行书以赵书为源,然能追二王之淳雅,唐寅在峭侧上力图脱出赵书,文征明则着力从挺拔劲健中间接晋人,相较而言,王宠离晋“韵”最近,他的行书是赵氏书风的反叛,但骨力稍欠,加之英年早逝,未然形成影响;邢侗直学王羲之书法,温润雅淡,与董其昌并称,但终不及董其昌影响深远。
近现代书家中,以沈尹默为代表,集合白蕉、马公愚、邓散木、潘伯鹰、李天马等,在碑学氛围中力求回归二王体系,形成当时的“二王派”,他们大都以行、草擅长,皆能出以文人“雅气”,他们的影响一直延至解放后,对碑学的泛滥起到一种“纠偏”的作用,在“碑学”形成俗态的关头,为书坛带来一股清气,同时,更在解放初的书坛占据主导,使二王行书体系再次复兴,沈尹默作为领袖人物功不可没。但从创作看,白蕉对二王体悟最深,被沙孟海称为“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沙孟海《题兰长卷跋》),在这次“复兴”中达到最高成就。
七十年代末开始,书法在长期寂寞之后进入蓬勃发展阶段,持续近二十年的“书法热”,将碑、帖的各种流派,各种风格都凸现出来,二王行书体系也再次全面复兴,无论是学米芾,学王铎,亦或学二王本身,皆洋洋大观,甚至形成“小行书风”、“手札风”等等,为书法的更加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王行书体系是一个庞大的书史系统,要想胪列清楚并非易事,上述线索只是给人提供一个认识的参照。从风格上看,二王行书体系内部呈观出来的表征虽然丰富多采,特别是这一体系中的那些大家更是各擅其胜,卓然独立,但从总体上说,无论是雅秀、雅淡、雅健,都脱不开一个“雅”字,这种“雅”是文人风采的外化,它既有“不激不厉”的温文,亦有沉厚痛快的雄健,从“雅”中的各取所需,各从所好,使二王行书体系在总体风格的统一下,斑斓多姿,亦复使书法史充满无穷的魅力。这是我们认识二王行书体系风格的一个基本视角和出发点;从书史传统看,二王行书体系的传承主要在文人圈内,是帖学兴衰荣枯的主要脉络,如果从根源而言,整个文人书法系统,都投射着二王书风的光辉,二王行书体系自然在其中占据特为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