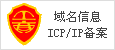作为华语电影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小金人,落在武侠类型片的头上实在是再适合不过。《卧虎藏龙》或许可以算是华语影坛最顶尖的一群高手,联袂奉献的武侠巅峰之作。李安导演,鲍德熹摄影,袁和平武指,叶锦添服设,谭盾配乐,加上马友友的演奏和一众演员的出色发挥,将儒家的淡雅冲和与道家的抱元守一在如诗般的画面中淋漓展示。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那个获奖季里,《卧虎藏龙》还收获了另外一个看起来不怎么搭界的奖项——雨果奖最佳科幻电影。中国人或许很难理解,江湖儿女,快意恩仇,怎么就科幻了呢?其实,对于并不习惯于飞天遁地、爆山裂石之类武侠美学的西方观众而言,《卧虎藏龙》完全可以当做是一群异能人士之间的战斗,而对武打设计更加夸张化和浪漫化的《东方不败》等影片,估计即便是将人物放进《X战警》中也毫无违和感。就像我们常常对印度影片里莫名出现的歌舞片段难以接受一样,观影习惯的不同文化的差异,早就了这个小小的冷幽默。
从影调来看,我们可以将整部影片划分为五个部分。开篇李俞二人重逢,俞秀莲独自赴京,将青冥剑交到铁贝勒手中,整个影调是明亮的,在青山竹林、古寨奢院的影影倬倬里呈现一派安详,让人沉下心来,用一种内敛的思绪来感受这一段故事。之后,玉娇龙黑夜盗剑,俞秀莲城墙缉凶,李慕白点拨娇龙以及碧眼狐狸与刘护院等人之战,影调转为冷峻灰暗,既符合隐藏在光明背面的江湖本质,又暗示着玉娇龙的明珠暗投。从闪回的玉娇龙与罗小虎邂逅开始,到娇龙离家出走,在酒楼上大战八方、威风凛凛,画面再转至明亮,从大漠黄沙的原始生命感和力量感,到飒爽英姿的剑走身飞,将“一遇风云便化龙”的脱困感与不羁的反叛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之后分别上演与俞李二人的两场足以名留影史之战后,影片又以暗与明两种色调分别描绘李慕白与玉娇龙之死,将一种超脱与救赎、愧疚与期待暗含其中。如此明暗相替,如同昼夜轮回,又好似梦境与真实的不断反复,李安的功力,于毫厘处妙至巅峰。
当年《卧虎藏龙》甫一问世,影迷骂作一片,评论界也大有厥词。普通影迷之不看好,大致是心理期待就有了错位,就像是抱着看《东成西就》的心态走进影院,结果看了一部《东邪西毒》,自然满身的不爽。而影评人的不满,则更多的是对影片本身的误读和未解。及至墙里开花墙外香,那边厢奥斯卡金人入手,大洋此岸许多人才重新审视,慢慢的品出其中的好来。
李安的作品本就是一杯苦丁茶,入口时只觉艰涩,入喉后才能从回甘中找到乐趣。
《卧虎藏龙》改编自王度庐小说,虽说古龙曾坦承,此公对自己影响颇大,但与同时期的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相比,王度庐应归于二流。他所开创的“悲情武侠”,无非是将张恨水等人的通俗小说写法,披上武侠外衣,无论从格局还是从影响来看,都略显渺小。不过正印证了一句老话:“一流小说改变二流电影,二流小说改变一流电影”。他的《卧虎藏龙》,经李安妙手点拨,竟成一代经典。而从受此影响而投身武侠的一种大陆导演和他们的作品来看,说此片彻底改写了中国电影,恐怕也不算妄言。
作为王度庐“铁—鹤五部曲”之四,《卧虎藏龙》之所以被导演选作原著文本,吸引之处,正在于那一份悲剧的艺术张力和角色的人格魅力。李慕白和俞秀莲,其实原本是前作《宝剑金钗》和《剑气珠光》中的主角,在《卧虎藏龙》原著小说中戏份不算太大。李安加重二人戏份,而将罗小虎的戏份大为删减,要的正是借助他们江湖儿女江湖老的阅尽沧桑,讲述李安心中的那一把青冥剑的故事。
李安最擅长的是心理剧。明明有万语千言在嘴边,等说出口却只是云淡风轻,只留无限思绪在那一举手,一投足之间,供观者把玩。这种心口难开,与李慕白与俞秀莲的故事有着天作之合。李俞二人好似《断背山》中的杰克与恩尼斯,明明爱欲炽热,却不得不因世俗的伦理和心中的块垒彼此逃避,抱憾终身。二人重逢,秀莲心中分明情似天高海深,到舌尖却只化作淡淡一句:“慕白兄,好久不见。”那一刻,我分明看见李安亲自化身《喜宴》中某个食客,在混乱的婚礼中娓娓道出一句,这,不过是中华五千年的性压抑。
所以,当李慕白握住俞秀莲的手,老神在在的说道: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其实,如同他送出青冥剑,意欲退出江湖,而当宝剑失窃,仇人现身,他心兹念之的,仍是一剑封喉的江湖恩怨。李安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青冥剑,放不下的,谁又能真的放下,松不开的,谁又舍真正松开。
李安借片中人物之口,以一种玄之又玄的武学“境界”,阐述着以道化人的幻寂与虚无。在得道与未得之间,李慕白感受到的,却是“被一种寂灭的悲哀环绕,这悲哀超过了我能承受的极限。”如同玉娇龙说到自己觉察到武功超过师娘的时候,并没有欣喜若狂,反而觉得“看不到天地的边”,心中惶恐得无以复加。而最后当李慕白行将圆寂之时,秀莲口中的“炼神还虚”,恐怕是指将一切放下的再无牵挂,而李慕白却最终用这一口气,说出了多年来阙如的那句表白,在两情相悦却缘悭一线的遗憾中魂归真武。一生的纠缠化作一个人的形单影只,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
玉娇龙人如其名,如飞龙在天,难被世情俗物所约束。在大漠狂沙中的策马奔驰,抵死缠绵,在酒楼上的惊鸿之剑,天外飞仙,让这个敢爱敢恨的女孩子,即使做了那么多搅乱一池春水的傻事,也让人恨不起来。但正是她性子里的刚久易折,伤害了身边的每一个人。李俞二人的悲剧,碧眼狐狸的怨恨,罗小虎的终生孤寂,甚至在原著小说中还有母亲的亡故与整个玉家的中落。而在“铁—鹤”系列的收官之作《铁骑银瓶》中,最终落得“龙归大漠、虎葬冰山”的凄美结局,王度庐的“悲情江湖”,至此达到巅峰。
但每每想起玉娇龙,我却总是在脑海中回想起聚星楼上那个英气逼人的身影。
“潇洒人间一剑仙,青冥宝剑胜龙泉,任凭李俞江南鹤,都要低头求我怜”。章子怡的美,于这一刻与玉娇龙合二为一,永远印刻在胶片上。
后来金庸在他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里,塑造了一个几乎与玉娇龙同模而出的人物——李沅芷。联想到古龙在自己集大成之作《绝代双骄》中,借“铁—鹤系列”的最初主角江南鹤之名稍作修改,生生造出“江别鹤”一角,温瑞安则在《神州奇侠》中,用《卧虎藏龙》续集的书名,编出“铁骑真人”与“银瓶道长”一对武林奇人。王度庐对香港一代武侠名家的影响,也就可见一斑了。
不少影评人,如徐浩峰在《刀与星辰》里将本片解读为情欲的追逐与肉体的赤裸,私以为是有些过分的。但书中另一篇文章,却对《卧虎藏龙》中的武打设计有着极其精彩的见解。当年本片被人诟病,其中理由之一,就是武打设计与大众审美的冲突。我们太习惯于武当剑法的以柔克刚,误以为李慕白的一触即发、后发先至看成杂耍,我们太执着于飘逸剑招的剑花璀璨,却把轻灵的步法看成向西洋剑法谄媚。就像徐浩峰所言,哪怕只考虑李慕白在竹枝上对玉娇龙眉心的一指,袁和平也无愧顶级武指的称谓。这种道家师徒仪式,象征着点化玄关的醍醐灌顶,非入室弟子而不得。此举不但符合李慕白武当大宗师的身份,也对人物塑造和叙事展开提供了意义。
几场重头武戏中,导演都使用了一种近景长镜头的拍摄手法,有时甚至用跟拍的方式,突显角色由武打风格而体现出的性格特色。在剪辑上,虽然不是一镜到底,但也彻底摒弃了时下流行的快速剪辑,整个打斗的节奏并不显得特别凌厉。城墙追逐战中,玉小姐的翩若惊龙,俞秀莲的大巧若拙,不但点出个人性格,也为她们的人生际遇埋下伏笔。镖局里的双姝对阵,俞秀莲连使刀钩锏剑等多般冰刃,信手拈来皆是文章,玉娇龙凭借宝剑之利与个性之狠始终旗胜一着,待到李慕白出手,她的轻巧却被李的厚重所完全压制,个人武功高下与气场强弱立辩。
与略偏写实的打斗不同,本片在对轻功的表达上走的是浪漫化的轻灵飘逸,竹林斗剑一场更是成为经典。有人说,李安是以竹为床,让白衣胜雪的两人上演一出欲拒还迎。无论如何,玉娇龙湿身后的玲珑曲线与二人眼神话语中的勾连暧昧,却是不争的事实。或许玉娇龙是真的爱上了李慕白,这样一来,她与俞秀莲的决裂与最终的离别都有了合理的解释。武当山上的纵身一跃,无论是看破红尘也好,为情而殉也罢,与一切作别,不带走一片云彩,飒爽如玉娇龙,本应如此。
原著小说中,玉娇龙借坠崖而遁,并在十九年后引出铁骑银瓶的故事。在电影里,李安却没有为我们交代更多线索。是生,是死,是看破,是逃避?随着马友友的提琴曲,故事落下帷幕,青山白云间,美人如玉,绝迹江湖。
影片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亮点当属配乐。谭盾的五线谱,为这个惆怅的故事赋予了一种舒缓的优美,将命运的无奈与红尘的纠葛娓娓述来,就像入口绵长悠远的竹叶青,令人迷醉。作为武侠电影,导演没有选择古典乐器,而是以大提琴和吉他为主旋律,把那种哀而不伤的愁绪、求而不得的反侧,如流水一般,默默融入电影的叙事当中,浑然天成。
谭盾与我父亲也算是颇有渊源,他们同岁且是校友,其住处又与我父亲的外祖父在一栋楼之中。遗憾的是父亲说谭盾当时总宅在家中,他只是听说过那户人家有一个与他同校的喜欢音乐的小孩,却一直无缘结识。不过家乡和母校出了一位大人物,父亲每每提起,也总自豪不已。可惜的是《夜宴》以后,谭盾的音乐重心渐渐转移到了舞台之上,于大银幕甚少涉足,也让我们少了几分耳福。这是题外话,略微一表。
虎卧龙藏,仇人授首,情人授心。李安借助王度庐的壳,用俞秀莲和玉娇龙两个女人的悲剧,成全了李慕白的道,也是他自己心中的道。这道的外在,是青冥剑,剑纹靡华却无坚不摧,折刀裂锏如断人心魂。这道的内在,是悲哀的寂灭,是逝友的亡魂,是不如归去的期许与承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存之于心,忘言于舌。